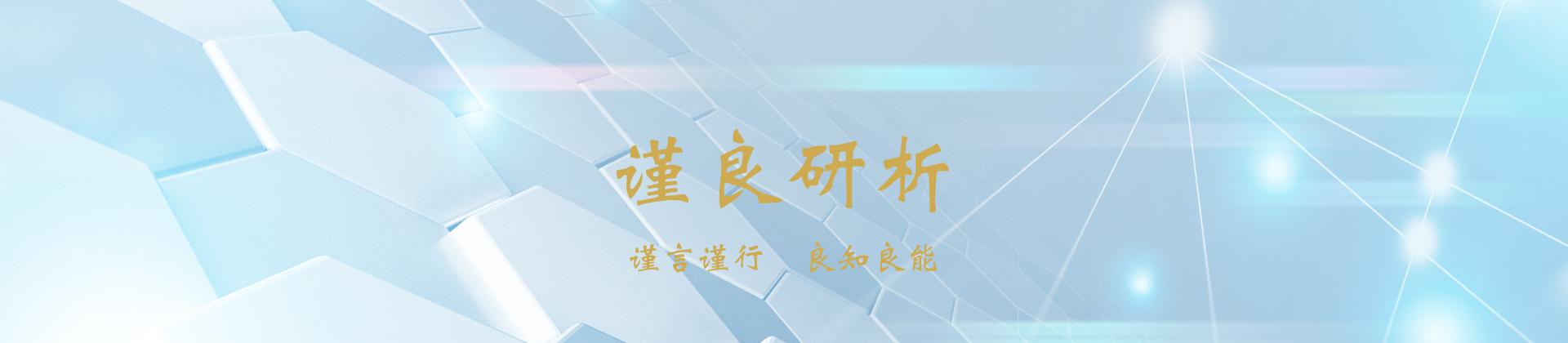
案件来源
谢某与贵州某名车行销售服务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4231号裁定书)
案件简介
贵州某名车行销售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小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11月1日公司的《公司章程》将股东持股结构变更为:刘小某持股51.9%、邓顺某持股20.7%、谢某持股9%、龙某持股9%、李宏某持股9%。
2012年3月12日谢某与股东刘小某签订《股权转让书》,约定:谢某将其持有的公司9%的股权转让给刘小某,刘小某支付谢某股权转让款7万元。之后,2013年10月26日、2014年2月26日司两次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予以修改,股东名册上均无谢某。
2014年11月1日刘小某、李宏某、宋某各转让2%、4%、4%股份合计金额20万元给谢某,并将《公司章程》中股东名册予以修改。公司原股东刘小某、李宏某、宋某以及新受让股东吴某、谢某,均在公司2014年11月1日的公司章程上签字确认、公司加盖公章认可。但该公司章程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2017年谢某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且提交公司隐瞒销售协议、未分配利润等证据,主张公司侵害其知情权。
案件焦点
1. 谢某的股东身份是否合法有效?
2.未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股东能否直接提起诉讼主张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裁判意见
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
最高院经过审理认为: 2014年11月1日,刘小某、李宏某、宋某各转让2%、4%、4%股份合计金额20万元给谢某,谢某已经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的义务,《公司章程》中股东名册部分予以修改,虽然此章程未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备案,但是公司的全体股东均在该章程上签字,章程内容未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符合法定程序,章程成立并生效,刘小某、李宏某、宋某分别与谢某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谢某取得公司10%股份的股东资格且已在公司章程中得以确认。
本案中谢某主张公司未在其住所地经营,实际经营状况不明,双方发生多起矛盾纠纷已不可调和,多次庭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拒不出庭应诉,谢某无法实现其股东知情权。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谢某在行使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知情权诉讼之前,需要先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理由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在股东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遭到公司拒绝提供查阅后,股东才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即谢某向法院主张股东知情权需履行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查阅目的等前置程序。其次,谢某在原审中提交的调查笔录只能证明法院基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需要所作的调查,未能体现谢某因行使股东知情权以书面形式向奔马公司提出过申请,原审以谢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股东知情权的前置程序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需要释明的是,股权知情权是公司经营或存续期间一个持续性的问题,谢某若有合理事由需行使知情权亦可再行主张。
综上,谢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最终裁定驳回谢波的再审申请。
本案心得
一、《公司章程》的效力
《公司章程》对外具有公众公示的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但对内而言,《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质,体现的是股东的共同意志,只要依法召开股东会,并且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达成一致,且内容未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股东就具有约束力,工商变更登记并非《公司章程》生效的必要条件,《公司章程》自股东达成合意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知情权行使的法定流程
作为公司的投资人、出资者,知情权是股东的法定权利,但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不宜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需依法依规进行。根据新《公司法》第57条的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流程如下:
(一)、股东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查阅的目的。公司应当自收到股东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若公司认为其查阅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
(二)、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实质是寻求司法救济,只有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才有赋予司法救济权的必要。如果股东未向公司提出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其权利行使是否受阻并不确定,直接赋予其诉讼权利便不具有必要性。
因此,股东提起知情权之诉,应当先履行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说明查阅目的前置程序,否则会被法院认定程序瑕疵而被驳回。

